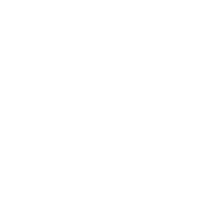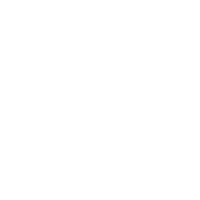□程 华
2007年1月,我的第一本公安题材报告文学集签约出版并由新华书店公开发行,印数5000册,后加印一次。当时我所在公安局宣传处领导喜形于色,要求将28万字全文连载于公安宣传网页上。事隔多年后,每每重阅这本曾经让我深感自豪的作品集,却总是凝滞卡顿无法卒读,一种羞愧总萦于心头:当年我怎么就有胆去结集出版它?
并非自己遣词造句的功力提升了多少,而是在阅历见识日渐丰厚之后发现,彼时自己对人物刻画过于肤浅,对案件事件叙述过于直白,导致文本标签化平面化:办案的一定智勇双全,干社区的一定细致周到,嫌疑人一定心狠手辣,受害人一定值得同情……的确,每个写作者在各个时期皆有特定的创作状态与水平,这是值得尊重乃至珍惜的客观规律。倘若回首生出“悔其少作”的喟叹,说明写作者已攀上较以往更高的层面。这其实很值得欣慰。
纵向回顾对比是一种自我反思总结,对于未来写作上纠偏补缺意义重大。这些年,我的纪实文学创作究竟是沿着什么轨迹在变化呢?前不久,一篇散文《我写“杨子荣”》令我感触颇深。作者胡杰是一名公安作家,多年来创作颇丰,包括纪实文学。当年,在案例写作小有斩获后,他试着给一本杂志投稿但屡投未中。何故?编辑点拨说,你把“座山雕”写得活灵活现,可是“杨子荣”呢?他顿悟:自己对案件的曲折离奇、嫌疑人的生存状态都不吝笔墨,却欠缺了对民警内心世界的挖掘。叙事不可谓不精彩,但民警成了案件背后的“人肉背景板”。尽管案侦过程自带看点,然文本的文学属性始终薄弱。如此,离纪实文学隔着很远的距离。
胡杰经历的过程,我正在经历。我正在将通讯转换为“文学”的路上跋涉。我不知走了多远还会走多远,但至少已经有了立“人”方能立“案”立“事”的主观认知。如今回览过去的版本,对于一桩案件的根源,我会以当前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去重新作出评判,而不是首先“啪”贴上固定标签;对于一个人物的内在,我会凭历经世事之后对于人性的了解去进行深度解读。人性何其纷繁复杂。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,何况人。
公安工作生活是题材富矿,此利。弊端也明显:写作者易掉入模式化的俗套窠臼。比如即将采写一位英模,写作者的思维容易事先设好定式并受其掣肘,这无疑会影响采访的方向和深度。采访完成后,又习惯性地将素材进行串联拼接,最后打磨成章。但我们真的深入触及采访对象内心了吗?真的读懂了每个人独特不可复制的甜酸苦乐了吗?我们有没有只注重对“先进事迹”的程式化搜集,忽略了凸显人性闪光点和能逆向反衬其不易的细节?我们在用惯了“英勇”“坚定”等词汇的时候,有没有想过运用更具体的细节来印证我们想要体现的主题?面对一个个采访对象,我们会否尝试将其置于宏阔的时代版图和琐碎的现实场景下去描写?
有的写作者历经数次采访挑灯撰写之煎熬,可谓殚精竭虑,民警却说“根本不像我们”。我想,正因为我们只“看”人未“读”心。这样千篇一律的稿子写出来只是在不断重复自我,其结果便是作者是作者,受众是受众,二者泾渭分明根本“两张皮”。如此语境下,无论文学创作还是典型宣传,都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和意义。
意识到这些短板并着力尝试去摒弃去规避,纪实文学创作才能真正开启前进的步伐。就公安纪实文学写作而言,除日常大量阅读之外,作者须具备丰富的阅历,包括对法律的把握,对公安工作的熟知,对公安民警群体的了解。
我在努力。我知道若干年后再看今天的文字,遗憾与自惭难免还会有。但希望不要太多。